 一、古龙:开局的大师与永恒的遗憾
一、古龙:开局的大师与永恒的遗憾
深夜,屏幕亮着。有人重读古龙的《楚留香之蝙蝠传奇》,忍不住发了一句:“这段看起来好像阿加莎的书。”不是简单的命案追凶,而是密闭空间里的人心博弈,是古龙用他特有的诗化语言和凌厉短句,搭建起的悬疑迷宫。
古龙是开局的大师。他写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,开头只有一句话:“冷风如刀,以大地为砧板,视众生为鱼肉。”瞬间将苍凉与杀意铺满纸面。他写《楚留香传奇》:“闻君有白玉美人,妙手雕成,极尽妍态,不胜心向往之。今夜子正,当踏月来取。”风流盗帅的形象跃然纸上。有在尝试写作的人回头去看古龙,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他到底有多厉害——他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都在寻求突破,变换写法,从《武林外史》到《绝代双骄》,从《欢乐英雄》到《七种武器》,他不愿重复自己。
“古大侠一直在变换写法,尝试突破自己。”可惜天不假年,留给世人一声叹息。但也有人看得豁达:“四季有时,没什么可惜的。他已经留了这么多作品给我们。”金庸、古龙这样的宗师离去后,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仿佛也随之落幕。他们的作品,连同那些被搬上荧屏的形象,曾是几代人珍贵的精神食粮,其地位犹如今天的网络文学,是当时年轻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构成。
二、网文时代:脑洞、评论与新的“江湖”
“现在是网文时代。”一句话道出了文化消费场景的变迁。武侠小说当年依托报纸连载,与读者一周一晤或数日一晤;如今的网络小说,更新以日甚至更短的时间单位计,读者通过章节说、评论区实时反馈,互动性远超以往。“网文读者反馈还更快,”有人比较道,“报纸可做不到每天雷打不动连载。”
网文的核心竞争力似乎转向了“脑洞”。“写的未必要有多好,但是一定要有惊喜。”层出不穷的设定、世界观创新成为吸引读者的关键。传统的“打怪升级开地图”模式已显疲态,读者渴求新鲜感。甚至有人调侃:“这么多脑洞写短篇多好。”意指许多创意撑不起长篇,但评论区本身有时却比小说正文更有戏剧性,“有时候评论比小说有意思”。这个时代的创作与阅读,共同构成了一场喧嚣的盛宴,只是不知其中能有多少沉淀为未来的经典。
也有人提到平台的多元化,甚至“外国网文平台”的兴起,但竞争无处不在,“国内都卷不过,换新平台卷未必能赢”。审核机制的存在是一个因素,但并非决定性的,“审核影响不大”,真正考验的还是创作者在既定框架下讲述精彩故事的能力。
三、专业的重量与“不讲武德”
“那个练武的不是说扳手都能打弯么,怎么打人脸就不行了?”有人发出疑问。随即有人点破:“特制的表演道具”,而“对面太坏了不肯配合表演”。这引出了“不讲武德”的调侃,但更深层的讨论是关于“专业”。
“任何牵涉职业化、明面或台面下有赌盘的东西,不尊重其专业的下场就是这样。”职业与业余的鸿沟在此刻凸显。通背拳师傅自己也说,去打格斗不合适。职业耳光选手经过专项训练,包括强大的颈部肌肉以抵抗冲击,甚至懂得在规则内运用技巧(如“消力”),而传武练习者往往缺乏这种针对性的实战和抗打击训练。“没练防御。这种规则,要把脖子那圈肌肉练粗练大才能扛,这哥们就没这个。”
讨论上升到普遍原则:“世界上没有一法通万法通这种事,尊重专业,就是尊重自己。除非你没有专业,才会觉得别人的专业没什么,自己也行。”就像练传武的去NBA打球会被轻易击败一样,隔行如隔山。问题的核心或许并非传武本身不行,而是“没经历过实战的传武不行”。两者的训练目标和应用场景存在根本差异。“职业的有一条很重要的是抗打击能力,一般传武不会针对训练这个。”
四、创作的考据:从圣斗士到静斗士
对话记录里还穿插着关于小说《妖刀记》角色和设定的讨论,尤其聚焦于一套被称为“雪貂拳证”的铠甲设计。众人将其与车田正美的《圣斗士星矢》和冷门作品《静斗士翔》(亦译作《隼骑士翔》)进行比较。
有人指出铠甲设计可能参考了圣衣的形态变化思路:“脸是在前面摊平?”随后被作者(默大)澄清:“是在背后摊开。”并附上示意图。对于读者调侃的“内裤摊开”式想象,作者幽默又带点无奈地回应:“我应该不会花这么多钱请绘师画一张这么蠢的图。”
讨论深入到设定本源。有人比较《静斗士翔》的铠甲动物特征更强,但缺乏圣衣的神话背景。作者详细解释道:“整个设定概念都不对。静斗士的设定是演化造成的外骨骼具现化,生物感比较强;圣衣则是神的意志化成的铠甲,是甲胄。”并进一步说明,圣衣根据等级(黄金>白银>青铜)包覆度不同,而静斗士受《圣斗士星矢》后期神圣衣影响,包覆度普遍很高。“更重要的是:我他妈就是拿圣衣当范例给绘师照着设计的!”——一句话道破了创作灵感的直接来源,也体现了作者对经典动漫文化的熟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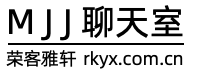
评论(0)